许晓东做点不一样的事
作者:今日大学生网 来源:今日大学生网
人物小传:许晓东,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,中国农业大学硕士,英国雷丁大学病毒学博士,主要研究杆状病毒的分子生物学。他历经10年持续探索,带领团队在病毒中首次发现了朊病毒,证实了“朊病毒广泛存在”的假说。人物小传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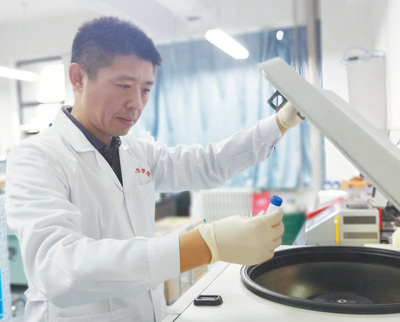 许晓东是幸运的。他是个想做点创新工作的普通人,在不经意间遇到了属于自己的研究课题,历经10年长跑,他以一篇论文短暂来到聚光灯下。回顾这段旅程,他承认这像一场冒险、一次与命运的拼搏。回到出发的原点后,他又开始在未知中重新探索。困惑与享受相互交织,他相信,走向纯粹的科学世界本就是这样。
许晓东是幸运的。他是个想做点创新工作的普通人,在不经意间遇到了属于自己的研究课题,历经10年长跑,他以一篇论文短暂来到聚光灯下。回顾这段旅程,他承认这像一场冒险、一次与命运的拼搏。回到出发的原点后,他又开始在未知中重新探索。困惑与享受相互交织,他相信,走向纯粹的科学世界本就是这样。
他们在《自然通讯》上发表的论文,被认为是证明朊病毒广泛存在这一“拼图”的最后一块
听到朋友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(以下简称“西农”)在网上火了,刘夏燕的第一反应是觉得不可能。
2019年1月的一天,“世界首例病毒中的朊病毒”话题登上了微博热搜榜。话题的主角是许晓东,刘夏燕很熟悉。10年前,她与丈夫郁飞回国来到西农生命科学学院。比他们稍早一些,许晓东与妻子陈红英从英国来到西农。
朊病毒是一类具有感染性的特殊蛋白。近40年来,科学家陆续在真菌和细菌中发现了它,但病毒中是否有朊病毒,一直不为人知。2019年1月,许晓东课题组在《自然通讯》上发表的论文,被认为是证明朊病毒广泛存在这一“拼图”的最后一块。
刘夏燕为许晓东高兴。她知道许晓东一直在默默研究大问题。消息出来后,同行四处打听许晓东是谁?在西农生命科学学院,不少人对他的了解仅仅是“做杆状病毒的”。
那时,许晓东已年过半百,只是一位副教授,回国多年没发几篇文章,无论从哪方面看,他都是一个有些平淡的人。
论文被《自然通讯》接受后,2018年底,许晓东在QQ空间写了一篇日记。透过日记,人们看到一位在冷门领域坚持做原创研究的学者。6万多人浏览、370人转发了这篇日记。
一年半后,记者见到了许晓东。他与陈红英共用一间不大的办公室,身材不高却很匀称,穿着老款的黑色衬衣,说话有东北腔,朴实无华。问起那篇日记,他突然非常不好意思:“我习惯在QQ空间记录实验进展,也就学生看看。当时情绪所至,写了几句,根本没想到这么多人关注。”
上了热搜,让许晓东猝不及防。媒体联系采访,他起初接受了几次,后来能推辞的,他都委婉谢绝。
“为什么不想大家讨论自己?”“我就是一个普通人。”许晓东缓缓地说。
困扰多年的心结解开,他觉得实验得出的每一个数据,每一张图都极为好看
许晓东曾在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中国农业大学教授陈文新门下读硕士。他曾告诉导师,自己想做点不一样的东西。得到老师的鼓励,他信心满满,想用当时刚兴起的DNA测序方法,做根瘤菌分类。
但研究生3年他过得异常痛苦,于是放弃了读博资格,转做行政。在中科院微生物所5年,他连升两级,从普通职员到科研管理处副处长,再到综合处处长。那时他30岁出头,做研究的念头时时在心里翻涌。
2000年底,陈红英到英国雷丁大学做研究,他跟着走出国门,一边学习一边打工,在大卖场扫地,在汽配厂开机床。有时在人来人往中,在机器的嘈杂声中,他出出神,想想头一晚阅读的文献。
一年后,他在雷丁大学找了个技术员的岗位。两年后,考上了博士。在科研这座围城中进进出出,这次回来,他说:“自己心静了许多。”
更大的冒险是科研选择。读博期间,在一次实验中,他意外发现一个名为LEF—10的杆状病毒蛋白信号异常。直觉告诉他,这背后有特别的含义。他查阅相关书籍、文献,没有找到任何记录。从英国到中国,他几乎逢人就问有没有见过这种现象,别人越说“没见过”“不知道”,他越兴奋:“我或许逮住了个新问题。”
没人愿意合作,这不难理解。投入不小,收益却看不到,这对科研,甚至对人生都无异于一场不对等的冒险。
鉴定朊病毒要用到一套酵母系统。朊病毒研究顶级专家、美国学者兰德尔·哈尔夫曼劝告他:“酵母系统很棘手,你们做不出来。”
美国专家的判断并非没有根据:全球做这套酵母系统的人源自同一个实验室,有手把手的“传承”。在纸面的操作流程外,还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,明明每一步都准确无误,就是没有结果。
很长时间,他茶饭不思,不吭声在实验室来回踱步。他本想速战速决,万万没想到,单是穿过酵母这道壁垒,就用了4年。
2017年9月的一个下午,许晓东团队完成了最后一项重要实验,至此困扰他们多年的心结解开了——异常就是病毒中朊病毒在“作怪”。他觉得实验得出的每一个数据,每一张图都极为好看,科研生涯中,他的成就感从未如此饱满。那个下午,他与陈红英、学生南昊,憧憬着未来,聊科学、侃人生,不觉夜色已深。
短暂走到聚光灯下后,许晓东回到原点,就像10年前一样
在那篇QQ空间日记结尾,他认认真真感谢了每一位给予过他帮助的人,写道:“我们终究是幸运的,终于看见了今天的朝霞。”
“如果没做出来,你会怎么办?”
“会等待机会,但我或许走不到终点。”许晓东的回答坦诚而平静。
到西农不久,郁飞担任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,几年后成为院长。由于长期考核殿后,不时有一些质疑许晓东的声音。闲聊时,郁飞常与人说起,许晓东夫妇家的车,节假日、周末都停在单位楼下,两个人常常泡在实验室,不像是在混日子。
他的信心还来自许晓东教课的良好口碑。他带的研究生课“高级生化”,总是在掌声中结束。本科上过他“分子生物学”的学生,到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读研究生,回来都感谢在他课上基础打得牢。
短暂走到聚光灯下后,许晓东回到原点,大部分时间,他没有头绪,就像10年前一样,他要不停思考、看文献。
他说,科研自身应该有一个世界,不应掺杂其他的东西。
中科院微生物所党委委员程萍与许晓东同龄。阔别近20年,程萍佩服这位老同事的勇气:如果没有冒这个泡,学术界有几个人会记住他?甚至没人记得他也在这上面用力过。
早在他转做行政时,身边很多人都判断,许晓东不可能重新回到学术道路上来。论文发表后,有人问:“西农的许晓东,是中科院微生物所那位吗?”
2018年夏天,许晓东到北京看望陈文新。陈老师已经90多岁了,师徒20多年没见,他们聊了3个多小时,从工作到生活,她询问许晓东过往的点点滴滴。当天,天气闷热,陈文新凝神聆听,当许晓东说起最新的研究时,这位昔日的恩师突然问道:“我记得,你不是说科研很苦吗,怎么最后又爱上了?”说完,她先笑了。
“你是陈老师喜欢的学生吗?”
“看到老师笑的时候,我相信老师会这么想的。”说着,他嘴角也露出一丝微笑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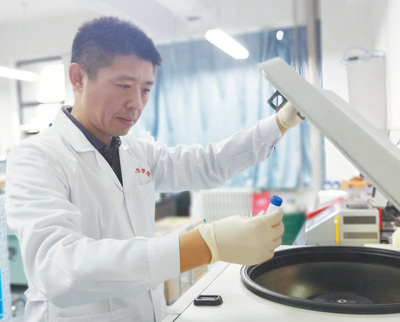
他们在《自然通讯》上发表的论文,被认为是证明朊病毒广泛存在这一“拼图”的最后一块
听到朋友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(以下简称“西农”)在网上火了,刘夏燕的第一反应是觉得不可能。
2019年1月的一天,“世界首例病毒中的朊病毒”话题登上了微博热搜榜。话题的主角是许晓东,刘夏燕很熟悉。10年前,她与丈夫郁飞回国来到西农生命科学学院。比他们稍早一些,许晓东与妻子陈红英从英国来到西农。
朊病毒是一类具有感染性的特殊蛋白。近40年来,科学家陆续在真菌和细菌中发现了它,但病毒中是否有朊病毒,一直不为人知。2019年1月,许晓东课题组在《自然通讯》上发表的论文,被认为是证明朊病毒广泛存在这一“拼图”的最后一块。
刘夏燕为许晓东高兴。她知道许晓东一直在默默研究大问题。消息出来后,同行四处打听许晓东是谁?在西农生命科学学院,不少人对他的了解仅仅是“做杆状病毒的”。
那时,许晓东已年过半百,只是一位副教授,回国多年没发几篇文章,无论从哪方面看,他都是一个有些平淡的人。
论文被《自然通讯》接受后,2018年底,许晓东在QQ空间写了一篇日记。透过日记,人们看到一位在冷门领域坚持做原创研究的学者。6万多人浏览、370人转发了这篇日记。
一年半后,记者见到了许晓东。他与陈红英共用一间不大的办公室,身材不高却很匀称,穿着老款的黑色衬衣,说话有东北腔,朴实无华。问起那篇日记,他突然非常不好意思:“我习惯在QQ空间记录实验进展,也就学生看看。当时情绪所至,写了几句,根本没想到这么多人关注。”
上了热搜,让许晓东猝不及防。媒体联系采访,他起初接受了几次,后来能推辞的,他都委婉谢绝。
“为什么不想大家讨论自己?”“我就是一个普通人。”许晓东缓缓地说。
困扰多年的心结解开,他觉得实验得出的每一个数据,每一张图都极为好看
许晓东曾在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中国农业大学教授陈文新门下读硕士。他曾告诉导师,自己想做点不一样的东西。得到老师的鼓励,他信心满满,想用当时刚兴起的DNA测序方法,做根瘤菌分类。
但研究生3年他过得异常痛苦,于是放弃了读博资格,转做行政。在中科院微生物所5年,他连升两级,从普通职员到科研管理处副处长,再到综合处处长。那时他30岁出头,做研究的念头时时在心里翻涌。
2000年底,陈红英到英国雷丁大学做研究,他跟着走出国门,一边学习一边打工,在大卖场扫地,在汽配厂开机床。有时在人来人往中,在机器的嘈杂声中,他出出神,想想头一晚阅读的文献。
一年后,他在雷丁大学找了个技术员的岗位。两年后,考上了博士。在科研这座围城中进进出出,这次回来,他说:“自己心静了许多。”
更大的冒险是科研选择。读博期间,在一次实验中,他意外发现一个名为LEF—10的杆状病毒蛋白信号异常。直觉告诉他,这背后有特别的含义。他查阅相关书籍、文献,没有找到任何记录。从英国到中国,他几乎逢人就问有没有见过这种现象,别人越说“没见过”“不知道”,他越兴奋:“我或许逮住了个新问题。”
没人愿意合作,这不难理解。投入不小,收益却看不到,这对科研,甚至对人生都无异于一场不对等的冒险。
鉴定朊病毒要用到一套酵母系统。朊病毒研究顶级专家、美国学者兰德尔·哈尔夫曼劝告他:“酵母系统很棘手,你们做不出来。”
美国专家的判断并非没有根据:全球做这套酵母系统的人源自同一个实验室,有手把手的“传承”。在纸面的操作流程外,还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,明明每一步都准确无误,就是没有结果。
很长时间,他茶饭不思,不吭声在实验室来回踱步。他本想速战速决,万万没想到,单是穿过酵母这道壁垒,就用了4年。
2017年9月的一个下午,许晓东团队完成了最后一项重要实验,至此困扰他们多年的心结解开了——异常就是病毒中朊病毒在“作怪”。他觉得实验得出的每一个数据,每一张图都极为好看,科研生涯中,他的成就感从未如此饱满。那个下午,他与陈红英、学生南昊,憧憬着未来,聊科学、侃人生,不觉夜色已深。
短暂走到聚光灯下后,许晓东回到原点,就像10年前一样
在那篇QQ空间日记结尾,他认认真真感谢了每一位给予过他帮助的人,写道:“我们终究是幸运的,终于看见了今天的朝霞。”
“如果没做出来,你会怎么办?”
“会等待机会,但我或许走不到终点。”许晓东的回答坦诚而平静。
到西农不久,郁飞担任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,几年后成为院长。由于长期考核殿后,不时有一些质疑许晓东的声音。闲聊时,郁飞常与人说起,许晓东夫妇家的车,节假日、周末都停在单位楼下,两个人常常泡在实验室,不像是在混日子。
他的信心还来自许晓东教课的良好口碑。他带的研究生课“高级生化”,总是在掌声中结束。本科上过他“分子生物学”的学生,到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读研究生,回来都感谢在他课上基础打得牢。
短暂走到聚光灯下后,许晓东回到原点,大部分时间,他没有头绪,就像10年前一样,他要不停思考、看文献。
他说,科研自身应该有一个世界,不应掺杂其他的东西。
中科院微生物所党委委员程萍与许晓东同龄。阔别近20年,程萍佩服这位老同事的勇气:如果没有冒这个泡,学术界有几个人会记住他?甚至没人记得他也在这上面用力过。
早在他转做行政时,身边很多人都判断,许晓东不可能重新回到学术道路上来。论文发表后,有人问:“西农的许晓东,是中科院微生物所那位吗?”
2018年夏天,许晓东到北京看望陈文新。陈老师已经90多岁了,师徒20多年没见,他们聊了3个多小时,从工作到生活,她询问许晓东过往的点点滴滴。当天,天气闷热,陈文新凝神聆听,当许晓东说起最新的研究时,这位昔日的恩师突然问道:“我记得,你不是说科研很苦吗,怎么最后又爱上了?”说完,她先笑了。
“你是陈老师喜欢的学生吗?”
“看到老师笑的时候,我相信老师会这么想的。”说着,他嘴角也露出一丝微笑。
责任编辑:周云 发布日期:2023-10-16 关注:
校园人物推荐
- 许晓东做点不一样的事
- 许晓东,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,中国农业大学硕士,英国雷丁大学病毒学博士,主要研究杆状病毒的分子生物学。
- 校园人物 10-16
- 一甲子坚守为“粮”心
- 雾蒙蒙的天空飘着如丝细雨,渭北旱塬的深秋处处透出寒意。
- 校园人物 10-16
- 张文宇扎根泥土 无悔青春
- 张文宇,男,我校理学院2018届毕业生,现任铜川市王益区王家河街道办事处主任助理、常家河村党总支书记助理、驻村工作队员。
- 校园人物 10-16
- 追忆朱显谟科学家的科学素养
- 1982年初春,我以硕士研究生身份进入水保所,第一次见到朱显谟先生。年过花甲的他看上去还很年轻,每天按时上下班,野外工作也很多。
- 校园人物 10-16
- 科学研究和群众智慧结合的典范
- 朱显谟先生是我的同志、我的好友,也是我的老师。在他90华诞之际,水土保持研究所和许多同行为祝贺他的科学人生
- 校园人物 10-13
- 朱显谟先生是我们的良师益友
- 朱显谟院士是我国近代土壤科学的奠基人之一,对我国土壤发生、分类和土壤资源的合理利用做出了杰出贡献。
- 校园人物 10-13
- 永远不能忘怀的老师——王建辰教授
- 从小学、中学到大学,我受教于众多老师,其中有一位我永远不能忘怀,那就是我在西北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学习期间的老师王建辰教授。
- 校园人物 10-13
- 毕生为河清——追记中科院院士、我校水保所研究员朱显谟
- 这个消息,对中国科学院院士、土壤学家和水土保持学家、我校水土保持研究所研究员朱显谟来说,是一个期待已久的喜讯。
- 校园人物 10-13
- 做国人满意的葡萄酒
- 黝黑的脸庞,朴实的笑容,坚毅的眼神。他用20年的执着与坚守,见证了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的发展壮大。
- 校园人物 10-13
- 探寻七秩足迹 传承红色基因
- 近日,哈尔滨工程大学有一群师生开启了一段漫长的探索校园之路,第一站来到陈赓大将的雕像,看看他们的故事吧!
- 校园人物 10-11
- 客服QQ:208830274今日大学生网©版权所有
- 社会实践报告投稿平台




